来自宇宙深处的呼唤
2024-11-01 00:15:02 | 作者: 匿名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基础物理与数学科学学院]
宇宙是一个相当大的地方。如果只有我们,似乎太浪费空间了。
第——章
外星人ET(图片来自网络)
您可能听说过ET 外星人,或者最近流行的三体人。但你可能不知道,有那么一刻我们几乎以为我们已经发现了它们!浩瀚的天空、星星、海洋一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星辰和遥远的岁月蕴藏着宇宙的终极奥秘。当我们仰望星空时,我们并不孤单。
2023年6月29日,北美纳赫兹引力波天文台(NANOGrav)、欧洲脉冲星授时阵列(EPTA)、帕克斯脉冲星授时阵列(PPTA)、中国脉冲星授时等多个国际脉冲星授时阵列合作组Array(CPTA)双双宣布,他们在最新的数据集中找到了支持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即——个具有引力波特征的四极相关信号。这一发现标志着继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直接探测引力波之后,我们即将迎来引力波物理领域的又一里程碑式突破。回顾历史,我们惊讶地发现,脉冲星与引力物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我们发现第一颗脉冲星时,我们验证了中子星的预测;当我们发现第一个观测双脉冲星时,我们间接探测到了引力波;当我们观察一组脉冲星时,我们会看到纳赫兹引力波的痕迹。还有亲爱的读者们,这个故事的开始只是关于ET的一个巧合~
来自“小绿人”—— Pulsar 的来电?
1967年8月,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休伊什教授的研究生贝尔像往常一样检查穆拉德射电天文台记录的数据。这一天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一道微弱的脉搏信号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发现信号的方向很不寻常。当她告诉导师结果时,他们最初认为这可能只是微弱的信号干扰。但人们很快发现该信号会重复出现,这意味着它很可能来自一颗“耀斑星”。从当年11月份开始,他们系统地分析了这个信号,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周期信号!这些信号由一系列脉冲组成,每个脉冲持续0.3 秒,重复周期约为1.337 秒[1]。这些脉冲保持极高的精度,并且来自天空中的固定方向。这种现象是以前的理论没有预测到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信号并不是来自地球的噪音,而只能来自宇宙深处!
左图是休伊什和贝尔观测到的第一个脉冲星信号,后来被编目为CP1919。右图是休伊什和贝尔对CP1919的首次观测结果。图片来自参考文献[1]
起初,休伊什和贝尔以为这可能是外星智能生物“小绿人”发出的信号(ET躲在角落里:什么?我被发现了),他们开玩笑地把这个信号给它起了个绰号“小绿人”。人”(LGM-1)。但科学研究需要注重证据,不能单纯依靠猜想(强调是后加的)。休伊什和贝尔并没有急于发表文章。相反,他们详细分析了该脉冲信号的各种特性,并寻求所有可能的解释。例如,数据的多普勒效应分析表明,该信号源相对于地球没有额外的轨道运动;这与“普通文明存在的行星会围绕其母星运行”的知识相冲突,所以基本否定了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最终,他们指出信号源位于太阳系之外,可能与白矮星或中子星等致密天体有关。后来,人们终于确认这是一种新型天体,并将其命名为脉冲星。
在休伊什和贝尔的文章发表两周后,英国乔德雷尔班克天文台发表了一篇文章,证实了脉冲星的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科学家们陆续发现了数个这样的脉冲信号;到1968 年,至少有8 个射电天文台观测到了脉冲星。脉冲星天文学时代就此开始!脉冲星与类星体、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星际有机分子并称为20世纪60年代天文学的“四大发现”。安东尼·休伊什教授本人因发现脉冲星而获得197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后来,科学家们逐渐认识到脉冲星是一种快速旋转的具有强磁场的中子星。他们的发现证实了我们关于中子星的理论预测。脉冲星很小(半径仅约10公里)且密度极高。如果你从它的表面舀出一小茶匙,它的重量相当于喜马拉雅山。脉冲星的强磁场导致其北极和南极发射高能射线。当这些射线射向并经过地球时,我们可以捕获无线电脉冲并准确记录它们的到达时间。它们就像宇宙浩瀚海洋中的灯塔,在宇宙中闪耀,精确地计算着每一分每一秒。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测量浩瀚的宇宙海洋。
左图是脉冲星的想象图。 (图片来自Bill Saxton,NRAO/AUI/NSF)右图是发现第一颗脉冲星的休伊什、贝尔等人的文章首页。 (图片来自参考文献[2])
在红外波长下拍摄的闪烁的蟹状星云脉冲星。该动画是通过将每秒30 转的频率调整得慢得多而获得的。 (图片由剑桥大学幸运摄影团队/维基共享资源提供)
1977年,“旅行者一号”和“旅行者二号”两艘飞船飞入宇宙深处,每艘飞船都携带着一张名为“地球之声”的镀金铜CD。这份记录上有14 颗脉冲星相对于太阳的位置图,由于脉冲星可以通过其电磁脉冲的独特时间来识别,因此我们的位置可以通过潜在的外星人来计算。十年后,最初被误认为小绿人的脉冲星,带着我们对外星文明的探索再次起航!这何尝不是一种浪漫呢?
航行者号的黄金唱片,左下角有脉冲星图。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他们正在互相接近——脉冲星双星!
受休伊什和贝尔工作的影响,泰勒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赫尔斯也开始使用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来研究脉冲星。他们首先关注脉冲星搜索的主题。 1974年,他们首次在21000光年外发现了一颗独特的脉冲星PSR B1913+16(数字中的PSR代表脉冲星,数字代表天体在太空中的赤经和赤纬)。这颗脉冲星以每秒17 次的频率向地球发射脉冲[3]。经过几年的观察,他们得出结论,脉冲星绕着一颗不太引人注目的中子星运行,它们一起形成了一个双星系统。这个脉冲星双星以及随后发现的其他类似双星系统,为广义相对论的各种精确检验提供了实验对象。 199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泰勒和赫尔斯,“表彰他们发现了一种新型脉冲星,这一发现开启了研究引力的可能性”。特别是PSR B1913+16的轨道周期约为7.75小时,但该周期衰减较弱,每年平均减慢76.5毫秒(误差为20%)。这种衰减与广义相对论对引力波的预测完全一致[4]。
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照片数据,拍摄于2019年春季。(图片来自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
脉冲星双星PSR B1913+16 的轨道周期随着引力辐射而衰减。图中的实线是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值,带有误差条的实线点是观测值。 (图片来自参考文献[4])
事实上,广义相对论预言,由于绕轨道运行的双星系统的加速运动,它们会拖曳周围的弯曲时空一起移动,由此产生的时空扰动将像湖面上的涟漪一样,以波浪的形式向远方传播。传播;这种波就是引力波。引力波在传播过程中会带走系统本身的能量,最终导致双星轨道周期的衰减。历史上,在我们发现双脉冲星之前,引力波是否真的存在一直是广义相对论领域的一个谜。就连广义相对论的提出者爱因斯坦也对这个问题没有把握。正是双脉冲星的观测数据,首次间接向我们提供了引力波存在的证据,从而坚定了科学界对引力波的信心!接下来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直接探测到引力波?
双中子星系统轨道产生的引力波的动画插图。 (图片来自NASA 科学可视化工作室)
使用一群脉冲星来测量时空涟漪!
前面我们提到,脉冲星被称为照亮宇宙的“灯塔”。其中一类灯塔特别特殊:它们可以在1秒内自转数百次,而且自转周期只有毫秒量级,因此也被称为毫秒脉冲星(Millisecond Pulsar,MSP)。这种脉冲星不仅旋转速度快,而且旋转极其稳定。即使在宇宙年龄的尺度上,它们的自转周期误差也不超过1秒!
当这种毫秒脉冲星扫过地球时,我们的射电望远镜可以探测到射电脉冲并准确记录脉冲的到达时间(TOA)。由于毫秒脉冲星的稳定性,理论上在人类活动的时间尺度内,我们预计脉冲到达时间之间的间隔几乎是恒定的,但实际上这些间隔会发生极其微小的变化。造成这些变化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地球的运动、星际介质的变化等。在数据积累过程中,我们将这些因素纳入到时序模型中,以拟合观测到的数据。如果定时模型预测的脉冲到达时间与实际观测之间存在差异(称为“定时残差”),则可能包含我们未包含在模型中的物理现象,例如望远镜噪声或引力波。从数学上讲,时间残差可以写成以下形式
其中表示模型误差引起的残差, 分别表示引力波和其他未知噪声源引起的残差。
如果我们可以同时监测许多这样的脉冲星,那么我们就有了脉冲星计时阵列(PTA)!通过不断观测和记录不同脉冲星脉冲的到达时间,我们构建了迄今为止宇宙中最稳定的“时钟阵列”,精确测量宇宙中的任何线索!
脉冲星计时阵列的插图。 (图片来自NANOGrav/T.Klein)
早在20 世纪70 年代,Sazhin 和Detweiler 就分别提出可以用单个脉冲星和地球组成干扰臂来测量极低频引力波[5,6]。然而,如前所述,影响脉冲信号到达时间的因素有很多。对于单个脉冲星,我们如何区分哪些因素是噪声?引力波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那个时代的人们。直到1983 年,Hellings 和Downs 才提出了一个关键见解:利用多个脉冲星组成阵列,通过测量不同方向脉冲到达时间的相关性,可以从噪声中提取引力波信号[7]。其依据是,一般噪声对于不同的脉冲星来说往往是相对独立的,但引力波则不同。广义相对论预测的引力波是四极辐射,这意味着当引力波沿轴传播时,时空沿轴被拉伸,沿轴被压缩,反之亦然。对应于脉冲星计时阵列,当两颗脉冲星与地球夹角较小(接近0度)或较大(接近180度)时,它们发出的脉冲会在引力波。到达地球后,计时残差呈正相关;而对于两颗近似垂直(接近90度)的脉冲星发射的脉冲,引力波引起的时间残差是负相关的。这种与角度相关的相关性(也称为“Hellings-Downs 相关性”)就像引力波的指纹,可以用来识别它!
左图显示了引力波在平面内沿轴传播的“+”模式和“x”模式。 (图片来自参考文献[8])右图为引力波背景的Hellings-Downs相关曲线。 (图片来自参考文献[9])
引力波在垂直于其传播方向的平面内沿某一方向传播的“+”模和“x”模的三维假想图。 (图片来自马克斯·普朗克引力物理研究所)
不同脉冲星定时阵列实验组测量的空间相关性和Hellings-Downs曲线的比较。 (图片来自参考资料[10-13])
但由于当时缺乏足够稳定的毫秒脉冲星,授时精度不够,直到1990年左右,Foster和Backer才首次使用了三颗脉冲星,PSR 1620-26、PSR 1821-24和PSR 1937+212 A使用多年的数据进行了实际尝试[14]。虽然他们当时没有得到很多实质性的结论,但这也为下一步发展利用脉冲星计时阵列寻找引力波背景提供了重要参考。
正当脉冲星计时阵列蓬勃发展之际,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2016年2月11日,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LIGO)协作组和处女座干涉仪(Virgo)协作组联合发表论文称,他们在2015年9月14日探测到了一个引力波信号。这个信号源自两个质量分别为太阳质量36 倍和29 倍的黑洞在距地球约13 亿光年处合并[15]。 LIGO 科学家Throne、Weiss 和Barish 也获得了201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LIGO探测到的引力波通常频率在几十赫兹到几百赫兹之间,属于高频引力波。脉冲星计时阵列搜索到的引力波信号频率在纳赫兹(nHz)频段,比LIGO低约10个数量级,属于极低频引力波。此外,还有探测毫赫兹(mHz)频段的空间引力波探测器,如欧洲的激光干涉空间天线阵列(LISA),以及我国的太极和天琴项目。他们的目标信号是低频引力波。不同频段的引力波探测器所能看到的物理信息有很大不同。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完整的引力波图景。
不同频段的引力波及其探测方法。 (图片来自美国宇航局)
LIGO的成功不仅结束了关于引力波是否存在的争论,还极大地启发了一系列引力波探测实验。目前,国际上有多个脉冲星授时阵列组织,包括北美纳赫兹引力波天文台(NANOGrav[16])、欧洲脉冲星授时阵列(EPTA[17])和澳大利亚帕克斯脉冲星授时阵列(PPTA[18])。 )、中国的脉冲星授时阵列(CPTA[10,19])和印度的脉冲星授时阵列(InPTA[20],InPTA是印日合作团体),都在积极积累数据,试图寻找纳赫兹引力波。
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新华社图片)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CPTA、北美NANOGrav、澳大利亚PPTA以及欧洲EPTA与InPTA联合于近期独立发布了引力波背景搜索成果[10-13]。四个合作组都发现了一个随机信号,其数据都不同程度地支持该信号具有Hellings-Downs相关性;其中,在中国天眼FAST望远镜的帮助下,CPTA获得了显着性为4.6倍标准差的观测结果。最接近粒子物理领域“科学发现”所需的5倍标准差金标准。
不同PTA合作小组报告的随机引力波背景信号。
脉冲星计时阵列、超大质量黑洞双星和引力波背景的艺术渲染。 (图片来自OzGrav ARC 卓越中心)
如果这个信号最终被证实是随机引力波背景,那么揭示其物理起源将是下一个最重要的科学问题。
超大质量黑洞的合并过程及其引力辐射。 (图片来自参考文献[24])
在这些不同的理论解释中,超大质量黑洞对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波源。科学家普遍认为星系中心存在超大质量黑洞[25]。当两个星系合并时,它们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逐渐下沉到合并星系的中心。它们不断与周围环境中的恒星、冷气体和其他物质相互作用,最终形成超大质量双黑洞系统。在双黑洞系统形成的早期阶段,它们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主导着演化过程,导致它们的轨道不断收缩。当双黑洞彼此接近的距离小于1 pc(相距约0.1 pc)时,它们的轨道演化将进入引力波主导阶段。在此过程中,双黑洞由于引力波辐射不断靠近,直至最终合并[26-28]。由于可观测宇宙中大量星系频繁合并[29,30],超大质量黑洞合并事件产生的引力波可以叠加形成引力波背景[21]。
除了可能的天体物理学解释之外,早期宇宙中发生的几个过程也可以解释该信号的起源[22,23]。例如,在宇宙早期辐射主导时期,标量扰动和张量扰动在非线性阶段相互耦合,导致标量扰动诱发引力波。早期宇宙中发生的一级相变以及某些相变过程中出现的拓扑缺陷也会驱动引力波的产生。他们穿越了十四亿年的星海,今天到达了彼岸!如果这个信号最终被证实具有宇宙学起源,它将能够揭示其他观测方法无法获得的关于极早期宇宙的信息,例如宇宙的物质状态以及小尺度原始宇宙的程度。密度扰动偏离正态分布。
我们宇宙的时间线、超大质量黑洞合并的起源和早期宇宙引力波的起源发生在不同的时间。 (图片来自BBC)

迈向未来
我们常常唱童谣“一闪一闪,一闪一闪,天空布满了小星星”。不经意间,那些满天的星星就会“飞进寻常百姓家”,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岁月无声,铭记四时的美食,宇宙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静静陪伴着我们;彩船云淡,星河升起,我们也用自己的浪漫感受宇宙的流动~
【参考】
[1] A.休伊什。 “脉冲星和高密度物理学”。 In: 修订版。物理。 47 (1975),第567572 页。 doi: 10.1103/RevModPhys.47.567。
[2] A.休伊什等人。 “观察快速脉动的射电源”。 In: Nature 217 (1968),第709713 页。 doi: 10.1038/217709a0。
[3] R.A.赫尔斯和J.H.泰勒。 “在双星系统中发现脉冲星”。 In: 天体物理学。 J·莱特。 195 (1975),第L51L53 页。 doi: 10.1086/181708。
[4] J. M. 韦斯伯格、D. J. 尼斯和J. H. 泰勒。 “相对论双星脉冲星PSR B1913+16 的定时测量”。 In: 天体物理学。 J. 722 (2010),第10301034 页。 doi: 10.1088/0004-637X/722/2/1030。 arXiv: 1011.0718 [astro-ph.GA]。
[5] M.V.萨金。 “探测超长引力波的机会”。年苏联Astron。 22(1978 年2 月),第36-38 页。
[6] 史蒂文·L·德特韦勒。 “脉冲星定时测量和引力波搜索”。 In: 天体物理学。 J. 234 (1979),第11001104 页。 doi: 10.1086/157593。
[7] R.w.海林斯和G. s.唐斯。 “脉冲星定时分析的各向同性引力辐射背景的上限”。 In: 天体物理学。 J·莱特。 265 (1983),第L39L42 页。 doi: 10.1086 /183954。
[8] G. Hammond、S. Hild 和M. Pitkin。 “未来地面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测器的先进技术”。 In: J. Mod。选择。 61(2014),第。 10.doi: 10.1080/09500340.2014.920934。 arXiv: 1402.4616 [astro-ph.IM]。
[9] 普拉文·库马尔·达哈尔。 “用于引力波研究的脉冲星计时阵列综述”。 In: J.天体物理学。阿斯特朗。 41.1(2020 年3 月)。 issn: 0973-7758。 doi: 10.1007/s12036-020-9625-y。 url: http://dx.doi.org/10.1007/s12036-020-9625-y。
[10] 徐恒等. “用中国脉冲星计时阵列数据发布一号寻找纳赫兹随机引力波背景”。 年(2023 年6 月)。 doi: 10.1088/1674-4527/acdfa5。 arXiv: 2306.16216 [astroph.HE]。
[11] 加布里埃拉·阿加齐等人。 “NANOGrav 15 年数据集: 引力波背景的证据”。 年(2023 年6 月)。 doi: 10.3847/2041-8213/acdac6。 arXiv: 2306.16213 [astro-ph.HE]。
[12] J. Antoniadis 等人。 “欧洲脉冲星计时阵列III 发布的第二次数据。寻找引力波信号”。 年(2023 年6 月)。 arXiv: 2306.16214 [astro-ph.HE]。
[13] 丹尼尔·J·里尔登等人。 “利用帕克斯脉冲星计时阵列寻找各向同性引力波背景”。 In: 天体物理学。 J·莱特。 951.1(2023)。 doi: 10.3847/2041-8213/acdd02。 arXiv: 2306.16215 [astro-ph.HE]。
[14] R.S.福斯特和D.C.巴克。 “构建脉冲星计时阵列”。 In: 天体物理学。 J. 361 (1990),第36 页。 300.doi: 10.1086/169195。
[15] B. P. Abbott 等人。 “观测双黑洞合并的引力波”。 In: 物理。莱特牧师。 116.6(2016),第116 页。 061102.doi: 10.1103/PhysRevLett。 116.061102。 arXiv: 1602.0383 7 [gr-qc]。
[16] 加布里埃拉·阿加齐等人。 “NANOGrav 15年数据集:个68毫秒脉冲星的观测和计时”。 In: 天体物理学。 J·莱特。 951.1(2023)。 doi: 10。3847/2041-8213/acda9a。 arXiv: 230 6.16217 [astro-ph.HE]。
[17] J. Antoniadis 等人。 “欧洲脉冲星计时阵列第二次数据发布I. 数据集和计时分析”。 年(2023 年6 月)。 doi: 10.1051/0004-6361/202346841。 arXiv: 2306.16
224 [astro-ph.HE]. [18] Andrew Zic et al. “The Parkes Pulsar Timing Array Third Data Release”. In: (June 2023). arXiv: 2306.16230 [astro-ph.HE]. [19] Rendong Nan et al. “The 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 (FAST) Project”. In: Int. J. Mod. Phys. D 20 (2011), pp. 989–1024. doi: 10.1142/S0218271811019335. arXiv: 1105.3794 [astro-ph.IM]. [20] Pratik Tarafdar et al. “The Indian Pulsar Timing Array: First data release”. In: Publ. Astron. Soc. Austral. 39 (2022), e053. doi: 10.1017/pasa.2022.46. arXiv: 2206.09289 [astro-ph.IM]. [21]Yan-Chen Bi et al. “Implications for the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binaries from the NANOGrav 15-year data set”. In: Sci. China-Phys. Mech. Astron. 66.12 (2023), p. 120402. doi: 10.1007/s11433-023-2252-4. arXiv: 2307.00722 [astro-ph.CO]. [22]Ziwei Wang et al. “The nanohertz stochastic gravitational wave background from cosmic string loops and the abundant high redshift massive galaxies”. In: Sci. China-Phys. Mech. Astron. 66.12 (2023), p. 120403. doi: 10.1007/s11433-023-2262-0. arXiv: 2306.17150 [astro-ph.HE]. [23]Zhu Yi et al. “Scalar induced gravitational waves in light of Pulsar Timing Array data”. In: Sci. China-Phys. Mech. Astron. 66.12 (2023), p. 120404. doi: 10.1007/s11433-023-2266-1. arXiv: 2307.02467 [gr-qc]. [24] Sarah Burke-Spolaor et al. “The astrophysics of nanohertz gravitational waves”. In: Astron. Astrophys. Rev. 27.1 (2019), p. 5. doi: 10.1007/s00159- 019- 0115- 7. arXiv: 1811.08826 [astro-ph.HE]. [25] John Kormendy and Luis C. Ho. “Coevolution (or not) of supermassive black holes and host galaxies”. In: Ann. Rev. Astron. Astrophys. 51 (2013), pp. 511–653. doi: 10.1146/annurev-astro-082708-101811. arXiv: 1304.7762 [astro-ph.CO]. [26] M. C. Begelman, R. D. Blandford, and M. J. Rees. “Massive black hole binaries in active galactic nuclei”. In: Nature 287 (1980), pp. 307–309. doi: 10.1038/287307a0. [27] Siyuan Chen, Alberto Sesana, and Christopher J. Conselice. “Constraining astrophysical observables of galaxy and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binary mergers using Pulsar Timing Arrays”. In: Mon. Not. Roy. Astron. Soc. 488.1 (2019), pp. 401–418. doi: 10.1093/mnras/stz1722. arXiv: 1810.04184 [astro-ph.GA]. [28] M. Dotti, A. Sesana, and R. Decarli. “Massive black hole binaries: Dynamical evolution and observational signatures”. In: Adv. Astron. 2012 (2012), p. 940568. doi: 10.1155/2012/940568. arXiv: 1111.0664 [astro-ph.CO]. [29] Eric F. Bell et al. “The merger rate of massive galaxies”. In: Astrophys. J. 652 (2006), pp. 270–276. doi: 10.1086/508408. arXiv: astro-ph/0602038.相关视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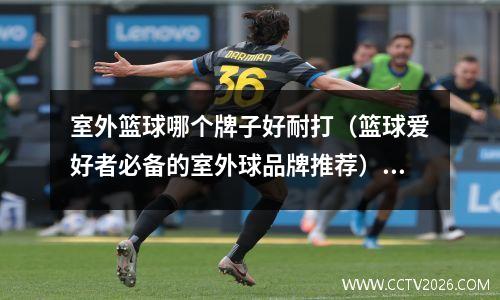
室外篮球哪个牌子好耐打(篮球爱好者必备的室外球品牌推荐)(室外篮球哪个牌子好用)
2023-09-0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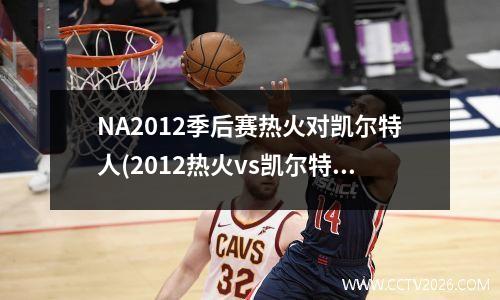
NA2012季后赛热火对凯尔特人(2012热火vs凯尔特人揭幕战)
2023-09-0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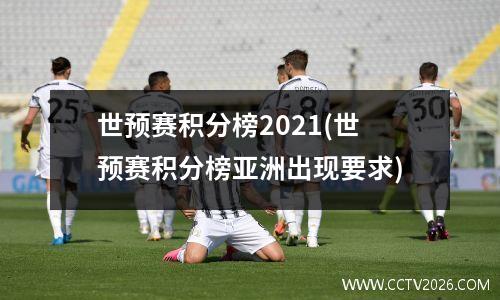
世预赛积分榜2021(世预赛积分榜亚洲出现要求)
2023-09-0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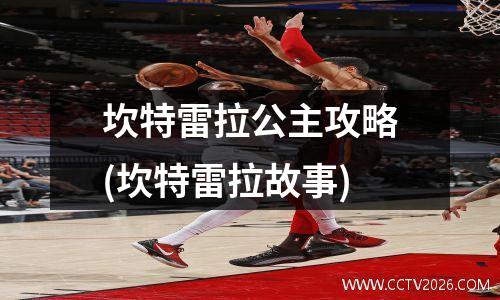
坎特雷拉公主攻略(坎特雷拉故事)
2023-09-07
-

谢尔盖米林科维奇萨维奇
2023-09-0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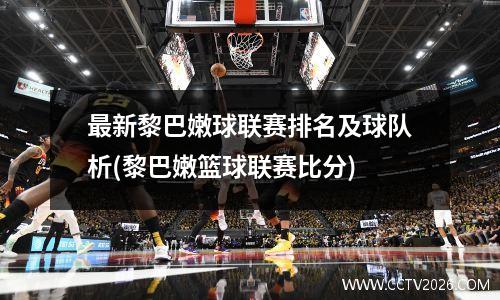
最新黎巴嫩球联赛排名及球队析(黎巴嫩篮球联赛比分)
2023-09-0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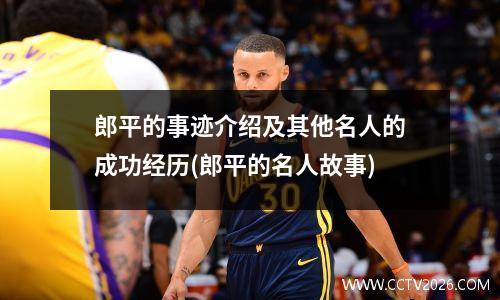
郎平的事迹介绍及其他名人的成功经历(郎平的名人故事)
2023-09-07
用户评论
哇,这篇文章真的太震撼了!每次读到宇宙深处的呼唤,我都仿佛能感受到那无尽的奥秘和宁静。感觉心灵都得到了净化。
有10位网友表示赞同!
我同意楼上,这篇文章让我对宇宙有了全新的认识。每次仰望星空,我都能想象到那呼唤的频率,太美了。
有17位网友表示赞同!
感觉这篇文章有点悲观,宇宙深处的呼唤仿佛在告诉我们,我们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这种感觉有点压抑。
有17位网友表示赞同!
我更喜欢这种悲壮的感觉,宇宙深处的呼唤让我想起了人生的无常,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刻。
有19位网友表示赞同!
这篇文章的文笔真好,把宇宙深处的呼唤描绘得如此生动,感觉自己的心都跟着呼唤飘向了宇宙的尽头。
有5位网友表示赞同!
每次读到这样的文章,我都会想起那首《来自天堂的呼唤》,感觉宇宙的呼唤和天堂的呼唤有着某种联系。
有9位网友表示赞同!
我觉得这篇文章的标题有点误导,宇宙深处的呼唤并不是一个绝望的声音,而是一种探索的勇气。
有17位网友表示赞同!
我有点好奇,宇宙深处的呼唤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那会是怎样的声音呢?
有11位网友表示赞同!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那个传说中的外星文明,宇宙深处的呼唤或许就是他们的信号。
有13位网友表示赞同!
感觉这篇文章的作者对宇宙有着深厚的感情,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对宇宙的敬畏。
有9位网友表示赞同!
宇宙深处的呼唤让我想起了那个古老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有16位网友表示赞同!
这篇文章的结尾有点突兀,感觉没有很好地呼应标题“来自宇宙深处的呼唤”。
有7位网友表示赞同!
我更喜欢那种神秘的氛围,宇宙深处的呼唤仿佛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对宇宙探索的大门。
有11位网友表示赞同!
感觉这篇文章的作者可能受到了科幻小说的影响,文中的一些描述有些过于夸张。
有15位网友表示赞同!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宇宙深处的呼唤应该是一种希望和力量,而不是绝望。
有5位网友表示赞同!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那部电影《星际穿越》,宇宙深处的呼唤就像是一种指引,引领我们探索未知的领域。
有16位网友表示赞同!
每次读到这样的文章,我都会想象自己能成为第一个听到宇宙深处呼唤的人类,那该有多酷啊!
有13位网友表示赞同!
宇宙深处的呼唤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解开宇宙的奥秘。
有14位网友表示赞同!